儿时砍柴记忆新
我今年64岁,生在农村,长在农村。乡下孩子早当家,六七岁就跟着拾柴火、捡稻穗、打猪草;年岁稍长,便要扛些重活。记忆里最清晰的,是十一二岁砍茅柴的日子。

老家砍柴分两种:硬柴要青壮劳力去大山里砍,耗上整整一天;茅柴是小山上的低矮杂树,男女老少都能去,小半天便能往返。生火做饭,硬柴耐烧,茅柴却少不了——它是最好的引火料。
我砍茅柴的日子,前后有两三年。到十五六岁,便跟着去大山里砍硬柴了。如今回想,那段时光里藏着我年少的懵懂,藏着祖父没说透的道理,更藏着我成年后才懂的滋味。

儿时印象里,祖父总在忙:要么下地做农活,要么侍弄屋后的菜地;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,白天在生产队种庄稼,抽空还要去大山里砍硬柴。看着他们起早贪黑的模样,我心里说不出的滋味,只盼着自己快点长大,能替家里分些担子。
约莫十一岁那年,祖父对我说:“书要好好读,活也得好好干。吃点苦不亏,将来不管做什么,都用得上。”说着,他给我备好了一套家伙:长短刚好的竹冲担、结实的钩索、能借力的打杵,还有一把磨得锃亮、带点弯度的茅柴刀。他还细细叮嘱:“走常有人走的山路,遇上同伴就一起;砍柴就去阳坡、坡缓,还能看见山下的人家,不害怕;独苗的小树别砍,留着让它长成材。”最后,他特意教我捆柴:“钩索要垫在柴捆最底下,柴得捆紧实,身后那捆要比身前的沉些——挑的时候借地势把柴穿在冲担两头,底端朝上,走起来才稳。”

第一次独自上山,大约走了三、四公里的田间小路和山路,是水漫山脉生产大队的桑叶场、茶林场周边的山坡,心里确实发怵,可走得多了,也就不怕了。每次挑柴回家,祖父从不多问砍了多少,只笑着迎上来:“累不累?先喝口水。”他眼神里的东西,我那时读不懂,如今想起来,满是疼惜。
后来我参军入伍,再后来在省城安家,退休多年。祖父已经走了37年,可每次想起砍柴的日子,他的话、他的笑,还有阳坡上暖融融的光线,都清晰得像昨天。就连当初不懂的“身后柴沉些”,也终于明白——原来那不是苛责,是教我把路走稳的智慧。


如今日子好了,没人再砍柴了,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液化气。当年砍过柴的小山,早已长满参天大树;竹冲担、钩索、茅柴刀,也成了记忆里的旧物。可那段时光教我的事,却像山间的泉水,一路淌进我往后的日子里:踏实做事,耐住辛苦,心里装着分寸。
原来,少年时砍柴的苦,从来不是苦。那是祖父用岁月慢慢酿的酒,越陈越暖,越品越醇。
上一篇:武穴吴氏文化《本修诗、词、文》
下一篇:已经是最后一篇
◆声明:本站属非营利性纯民间公益网站,旨在对我国传统文化去其糟粕,取其精华,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做一点贡献。所发表的作品均来自网友个人原创作品或转贴自报刊、杂志、互联网等。如果涉及到您的资料不想在此免费发布,请来信告知,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予以删除。 全部资料都为原作者版权所有,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能下载作为商业等所用。——特此声明!
相关内容
- 2025-11-12 武穴吴氏文化《本修诗、词、文》
- 2025-11-11 王仙三狮仙赋
- 2025-11-10 二龙米粉
- 2025-10-25 夜饮
- 2025-10-17 教孩儿之歌
点击排行
- 104-08县城里的小孩,人们,与游戏
- 203-17越绝书一
- 303-17越绝书二
- 401-30吴三桂诗词文艺汇编 (一)
- 501-15吴称谋诗词—— 参禅悟道...
随机文档
- 110-22凡事做到极致便是成功
- 207-06真正聪明的人,往往深藏不露
- 301-03吴敬业世系长益房性熙支源流序
- 403-13福建社坛村桥仔头吴氏祖宇...
- 501-25吴氏族谱的二十五问之五:...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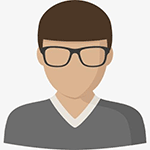


看你合肥柴火第一张图,和我们小时候一样的捆柴法。儿时,每当周末,我们都要到屋背山上去砍柴。一天一挑。到放寒暑假时,每天两挑。当时没有电,全靠柴。
2025-11-13 09:18:21 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