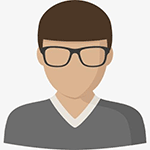在越南,拜谒王勃墓
破晓时分的蓝江入海口,咸湿的海风裹挟着北回归线以南热带雨林特有的气息,让我的衣衫沾染了半湿。
对岸的椰林在晨雾中若隐若现,几艘渔船正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撒网。越南向导映雪指着不远处一片隆起的高地:“那就是唐朝诗人王勃的安息之地。”

王勃墓大门
穿过一片被弹痕刻满的椰树林,铁丝网围起的遗址赫然跃入眼前。谁也无法想象,大唐最耀眼的文星,最终陨落在这片热带土地上。
王勃墓园坐落在越南义安省宜禄县宜春乡蓝江左岸,1972年美国对越南实施的大轰炸,将这座墓园尽毁,唯有几块唐代风格的砖石半埋在红土中,隐约拼凑出祠庙曾经的轮廓。
令人动容的是,废墟中央新立的花岗岩墓碑——上面同时镌刻着中文和越文:“唐诗人王子安之灵位”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墓园,是后来当地民众自发集资修建的,包括祠庙、围墙和碑亭。

王勃墓
亭下,一块斑驳的墓碑,历经岁月洗礼,碑文已模糊不清,无法辨认。碑前的石案上,摆着满满的供果,香炉里积着新鲜的香灰,显然常有人来祭拜。
听向导映雪介绍,每天清晨都会有个老人来清扫。正说着,一位驼背老者蹒跚而来,手里拿着扫帚和鲜花。他就是75岁的越南老兵阮文雄,当年冒死从炸毁的祠庙中抢救出王勃雕像的人。
“木像的左脚被火烧过,”老阮抚摸着墓碑上的刻字说,“但面容还看得出是中原人的清秀。”他打开手机相册,照片中的雕像头戴唐巾,身着宽袍,右手虚握如持笔,眉宇间凝着跨越千年的孤傲。
站在王勃最终安息的土地上,我禁不住思绪万千。遥想龙朔元年(661年)的长安,11岁的王勃正在弘文馆诵读《诗经》,已是名动京城的“神童”。其祖父王通是隋末大儒,叔祖王绩开创“山水田园诗派”,父亲王福畤官至太常博士。

滕王阁
这个河东王氏家族,自汉末以来就以文采传家。“六岁善文辞,九岁得颜师古注《汉书》读之,作《指瑕》以擿其失。”我对着蓝江滔滔水流喃喃自语。江水呜咽,似在回应我的追思。
15岁向宰相刘祥道上书言政,16岁应幽素科及第,授朝散郎——这般履历,纵览中国文学史亦属罕见。更难得的是他17岁所作的《乾元殿颂》,竟让唐高宗连叹三声“奇才”。
江风突然转急,浪花拍岸声恍若长安宫殿里的钟鼓。我想象着麟德三年(666年)的春天,少年得志的王勃如何以从七品朝散郎的身份,随驾参加泰山封禅大典。
他骑马走在仪仗队中,锦袍玉带,目若朗星,笔下流出“云销雨霁,彩彻区明”这般预言盛唐气象的句子。
然而,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。乾封元年(666年),沛王李贤与英王李显(即后来的唐中宗)斗鸡取乐,王勃助兴而作《檄英王鸡文》,写下“两雄不堪并立,一啄何敢自妄”这样的戏谑之词。
谁能料到,这篇游戏文字竟触动了高宗最敏感的神经——太宗玄武门之变的惨痛记忆尚未消退。“即日斥勃,勿令入府。”圣旨一下,王勃被逐出长安。
我在墓园里蹲下身来,抓起一把红土,灼热的触感仿佛千年前那个青年才俊被赶出王府时的羞愤。蓝江对岸有鸡鸣声传来,恍惚间竟似听见历史的嘲讽。
被逐后的3年间,王勃漫游巴蜀。在峨眉金顶,他写下“长江悲已滞,万里念将归”;在锦官城外,吟出“乱烟笼碧砌,飞月向南端”。这些诗篇已透露出从华丽辞章向深沉意境的转变。
咸亨二年(671年),王勃任虢州参军期间遭遇人生最大劫难。关于那个叫曹达的官奴之死,新旧唐书都记载模糊。但站在交趾(现越南)的烈日下细想,一个曾得皇帝赏识的才子,怎会无故杀死官奴?更可能是陷于官场倾轧,毕竟他曾在诗中自陈“耿介不偶俗,是非空自持”。

滕王阁近观
上元二年(675年)秋,王勃南下交趾省亲。途经洪州时,恰逢都督阎伯屿重修滕王阁大宴宾客。那个重阳佳节,26岁的王勃在酒酣耳热之际,接过纸笔写下“豫章故郡,洪都新府”。
我忽然明白为何《滕王阁序》能成为千古绝唱。那是王勃用全部生命经验凝练的华章:有“时运不齐,命途多舛”的感慨,有“老当益壮,宁移白首之心”的倔强,更有“北海虽赊,扶摇可接”的希望。
当写到“阁中帝子今何在?槛外长江空自流”时,他是否已预感到自己也将如帝子般转瞬即逝?
据越南《大南一统志》记载,王勃于上元三年(676年)初夏抵达交趾。在宜禄县的刺史府衙遗址旁,我找到了可能是王勃与生活窘困的父亲相聚之地——一处唐代风格的建筑基址,虽然已被后来的建筑覆盖,但地基的莲花纹砖明显是初唐样式。
当地85岁的老祭司阮文泰告诉我,族谱记载他的先祖曾见证王勃父子相见:“诗人穿着褪色的唐装,跪在父亲面前久久不起。”这个场景在王勃的《上百里昌言疏》中得到印证:“如勃尚何言哉!辱亲可谓深矣。诚宜灰身粉骨,以谢君父……”王勃在交趾陪伴父亲3个月后,于秋八月乘船启程北返,行至蓝江入海口时,遭遇突如其来的风暴。
当南海的巨浪吞噬帆船时,可曾知道它卷走的是怎样一颗文星?潮水将他的遗体送回蓝江岸畔,交趾百姓认出那位在滕王阁写下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的青年,于是将他安葬在红壤高坡上,面朝北方的中原。

登滕王阁观落日
如今,站在墓址眺望,只见菠萝蜜树在烈日下投出斑驳阴影,几个越南孩童在废墟间追逐嬉戏。他们不知道,这片长满野芒的土地下,安息着整个盛唐文学的黎明。
我乘坐的渔船行至当年出事海域,船公指着远处泛着白沫的漩涡区告诉我:“就是那里,老辈人说诗人的船是被龙卷风掀翻的。”夕阳西下,整个南海被染成金红色。
恍惚间,我看见一叶扁舟在惊涛中挣扎,那个27岁的青年紧紧抱着写给父亲的诗稿。咸涩的海水灌入口鼻时,他是否想起滕王阁上的欢声笑语,是否遗憾未完成的诗篇?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我忽然顿悟:这千古名句写的不仅是鄱阳湖,更是诗人预见的生命终点——那落日熔金般的壮美,孤鹜挣扎的凄绝,水天相接的永恒。
回到岸上,老阮邀请我去他家瞻仰王勃木雕像。雕像供奉在厅堂正中的神龛里,前面摆着新鲜的水果和香炉。
令人惊讶的是,旁边还供着一本越文版的《滕王阁序》。“我们这里的孩子都要背‘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’。”老阮的孙女阮氏梅用流利的中文说。她告诉我,义安省的中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来王勃墓遗址朗诵诗歌,“王勃在我们心中,就像你们的李白杜甫一样重要”。
夜幕降临时,村民们聚集在遗址前举行每月一次的诗歌晚会。老人们用古越语吟唱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,孩子们表演根据王勃生平改编的水上木偶戏。当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的诗句在椰风中回荡时,我忽然明白:王勃早已成为连接中越文化的永恒桥梁。
深夜独坐蓝江边,看渔火点点。老阮拿来家藏的《王勃诗集》越文译本,扉页上写着:“诗人虽死,诗意永存。”是啊,王勃肉身虽逝,但他的诗魂早已跨越国界。
在山西河津故里,在江西南昌滕王阁,在越南义安省,在所有被汉字文明浸润的土地上,人们用不同的语言传诵着同一个天才的故事。那个写下“天高地迥,觉宇宙之无穷”的青年,最终化作宇宙间永恒的存在。
蓝江水在不远处呜咽。当地老人说月夜常能听到吟诗声,用他们听不懂的中原官话。我静立良久,似有朗朗诵诗声传来。每当海潮拍岸,那汹涌的波涛便化作磨墨的砚台,将南海万顷碧波研成永不枯竭的墨汁;每当风过椰林,那沙沙的叶响便成了诗人吟哦的平仄,在热带的天宇下续写着未完成的诗篇。
27岁的生命或许短暂,但天地却以永恒的方式为他执笔——浪花在礁石上写下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注脚,季风在沙滩上勾勒“天涯若比邻”的轮廓,就连珊瑚丛中闪烁的磷光,也都是散落的诗眼,在深海中明明灭灭。这绵延千里的海岸线,何尝不是一轴无尽的长卷,让那位早逝的诗人,得以继续他被海浪中断的歌唱。
离去时,朝阳正从南海的边际喷薄而出,万道金光洒在蓝江粼粼的水面上。江风拂过,泛起无数金红交错的光斑,犹如千片碎金在碧绸上跳跃舞动。
恍惚间,一只孤鹜掠过水面,它的剪影在晨光中划过优美的弧线,竟与千年前鄱阳湖上的那道晚霞中的孤影别无二致。
这一刻,时光仿佛折叠,空间已然消融,让人顿悟:原来真正的诗魂从不曾离去,他们只是化作了天地间的气息,融进了山河的脉搏,在每一个被吟诵的诗句里获得重生。
在这片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红土地上,王勃的墓园或许简陋,也不引人注目,但他的诗篇早已在时光的长河中筑起不朽的丰碑。
那碑不在石头上,而在每一个向往美的心灵里;那墓不在泥土下,而在每一轮照耀过唐诗的月光中。
当世界各地的游人至此凭吊,当越南的学子用异国的声调吟诵“天涯若比邻”,当中国的旅人在异乡听到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越语翻译,王勃的生命就在这一次次的文化回响中延续。
此刻,我站在蓝江入海口,看着那片曾经吞噬天才的海域,忽然明白:每一次《王子安集注》被翻开,每一次“落霞与孤鹜齐飞”被吟咏,都是时空隧道的一次开启,让我们得以与那位27岁的诗人重逢。
他的生命虽然永远定格在青春的年纪,他的诗魂却随着南海的潮汐涨落了千年,随着每一阵掠过椰林的风声传诵不息。
这或许就是文学最大的奇迹——让一个生命突破时间的囚笼,让一片诗心跨越疆域的界限,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
朝阳愈升愈高。我最后回望那座简陋却又不凡的墓园,心中恍然:王勃从未长眠于此,他与天地同在,与诗歌同辉,在这片他曾经踏足的土地上,永远地活着,永远地年轻着。
上一篇:至德宗亲十二姓渊源简介
下一篇:已经是最后一篇
◆声明:本站属非营利性纯民间公益网站,旨在对我国传统文化去其糟粕,取其精华,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做一点贡献。所发表的作品均来自网友个人原创作品或转贴自报刊、杂志、互联网等。如果涉及到您的资料不想在此免费发布,请来信告知,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予以删除。 全部资料都为原作者版权所有,任何组织与个人都不能下载作为商业等所用。——特此声明!
相关内容
- 2025-11-05 至德宗亲十二姓渊源简介
- 2025-10-15 中国姓氏为何能传承数千年,最早的姓氏起源与什么有关?
- 2025-10-12 揭秘中国十大罕见姓氏:每一个都藏着千年故事
- 2025-05-26 乙巳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隆重举行
- 2025-04-30 孟子故里邹城举行纪念孟母孟子大典
点击排行
- 102-09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...
- 203-18会同,有个连山炎帝故里?
- 303-02晋江小兴源道坛沿革浅谈
- 412-01贵州三穗民间姓氏故事
- 502-27与先祖对话,寻迹江上家园...
随机文档
- 108-06安塘三里祭祖
- 210-12湖南新晃吴世万后裔寻祖归...
- 312-12太伯74世晳祖6世之蒨公
- 406-12太学生兰轩四弟传赞
- 511-27换个角度看人生,你的生活...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